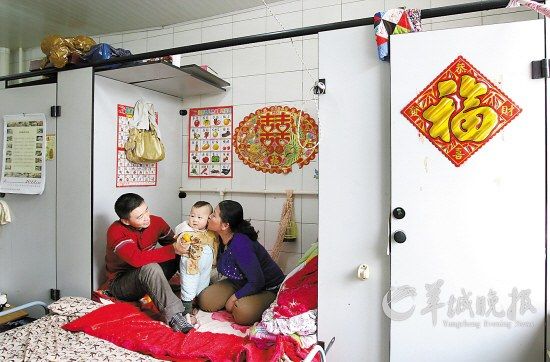涧道雄关
在没有修建金兰、沙畈两座水库之前,绵延百里的白沙溪是山民们运输竹、木、炭等货物的主要交通要道。山民们把竹子和木头捆扎成排,随着水势顺溪而下。等出售完山货后,再换回大米等各种日常用品。不过出山容易进山难,回去的时候,撑竹排显然是行不通了。这时候,只有用最原始的挑担的方式,沿着白沙溪的涧道,一步步往大山深处的家中挪动。
从琅琊古镇进山后,依附于白沙溪而建立的村庄可谓星罗棋布。不过,这些小村庄基本上都只有几户人家组成。只有经过乌云的石拱桥后,才出现了一个叫周村的大村落。这个村庄有一座规模较大的祠堂,祠堂里有一个精美的古戏台,每到逢年过节,总要演几出才子佳人和出将入相的地方戏。
周村地势开阔,田原肥美。一直到石坞、高儒、亭久等几个村庄为止,一大片平整的农田,是这座山沟沟里难得一见的景观。不过,从周村再往深山行进后,山道开始渐渐险峻,白沙溪也由此变得桀骜不驯了起来,它时而隐在青山深处,时而又在过了一道山岭后冷不丁地奔腾而出,令你防不胜防又惊喜莫名。
1935年2月,粟裕将军率部挺进浙江,随即进入浙西南开辟了新的根据地。而这条白沙溪流域,就是粟裕当年实行正规军到游击队战略转变的地方。他就是在这片涧道雄关上,创造性地积累了武装斗争与游击战术相结合的新经验,并为此后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的成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1年,将军病重期间,依然念叨着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在他的指示下,一条从白龙桥到遂昌县门阵村的白沙公路得以顺利修建。
在这条白沙公路没有修建之前,山民们基本上是靠着一条白沙涧道出行的。这条涧道在一个叫柿树岭的村庄开始分成了两道山沟,一条从半溪、黄加田、水碓基、然后在将军坑翻越数道险关后,可以直达过去的宣平县。这个宣平县的莲子非常出名,号称宣莲,是旧时皇家的专用贡品。1958年,宣平县被撤消,原有的所属地域分别被划归毗邻的莲都、松阳、武义三地管辖。另一条从芝肚坑、小洋坑、银坑,然后到达遂昌的门阵村,经遂昌再达闽、赣等地。遂昌是一座千年的山城,中国古典名剧《牡丹亭》,就是汤显祖在任职遂昌县令其间创作完成的。
由于位于金华、武义、遂昌的三县交界,这里的老百姓都会说好几种方言。在战乱纷争的年代,更有大批从南京、福建等地的先民迁徙到此繁衍生息。在溪口的田莆村,村民们操的是福建话。而在相隔不远的黄加田村则说的是南京话,有时由于相互嫁娶的原故,一个村庄甚至一个家庭里,也是多种语言杂陈,但彼此之间的沟通却丝毫不受言语差别的影响。
在这条古老的白沙涧道上,处处乱石嶙峋,时时险象环生。有的巨石如溯水神龟,有的垭口似饿虎捕食,更有那数不清的巍峨雄关,分布在沟壑纵横的白沙古道上。在战乱频发的年代,这些铁道雄关很好地护佑了山民们的安宁。岁岁年年,从各地避乱于此的先民们已经在白沙溪畔深深地扎下了根,尽管仍旧操着各自的母语,但是日久他乡成故乡,他们显然已经把自己的血脉,永远地留存在了白沙溪畔。
白沙溪是道不尽的,就像白沙溪上的鹅卵石是数不清的一样。我所描述的白沙八景,只是白沙溪上无数景观中极小的一部分而已。我有限的学识更是表达不出白沙溪的无限之美。然而,我仍然愿意用我并不流畅的笔尖,来抒写对这条溪流的热爱。因为我和千百年来被白沙溪养育的无数百姓一样,也是一个白沙溪的孩子。
我多么希望变成一粒石子,永远地依偎在白沙溪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