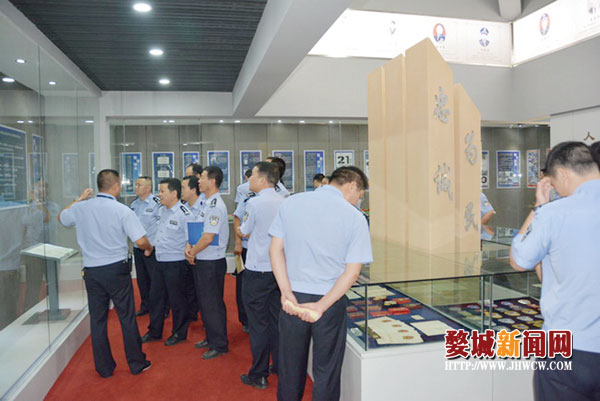洞叭坞是金华汤溪镇去城南十五里左右的一个小山谷,多年以来,它鲜为外人所知,如今更是无人提及。
多年以前,我在其中割草、放牛、摘花,在林子里疯跑,洞叭坞的春天是满山遍野的杜鹃。那些深红色的、粉红色的、浅紫的、粉白的,一簇簇一团团,拥挤在一起,争先恐后地涌来。她们的笑脸都那么灿烂,你分不清到底谁是谁,哪一朵更美,她们环绕在你的脚边,环绕在你前面、后面、左边、右边,你抬头看也是,低头看也是,胆小的含羞敛眉,胆大的站在高坡,迎风怒放。她们吵吵嚷嚷的,细小的喉咙里发出无数的叫喊,吵得整座山都沸腾起来。马尾松们、黑松们、樟树们、栎树们,脑袋都被吵大了、吵昏了,昏昏欲睡,春天嘛!春眠不觉晓嘛!但是他们微笑着,一言不发,忍受着这个宁静世界的喧闹。她们小小的花瓣那么单薄,又那么自然鲜艳,像这大山里扎着麻花辫、穿着花布衣、不施脂粉的乡下妹子。有时候她们鱼贯而行,高低错落;有时候又挤成一团,你的胳膊伸到我的脸上,我的大腿叉到你的腰;有时候又规规矩矩地并排蹲着,蹲得低低的,两张脸贴在一起,拘谨得好像乡下妹子第一次上城照像。这满目的花朵是大山胸膛里按捺不住的春意。仿佛从冬天开始,它们就开始蕴蓄,在骨头里、血液里、心脏里,一点一点地增加暖意。太阳一天天高起来,它们冻僵的血脉天始流畅,它们的头发生长得很快,身体不安起来、灵活起来。几场春雨一下,春风一吹,蕴藏在体内的力量、欲望、喜悦、新奇和不安,像地底灼热的熔岩,冲破皮肤、骨头、心脏、毛细血管,一齐爆发出来,从山顶到山脚,流淌了一地。
从曹界村出发,到达洞叭坞,必须步行。出了村,走过一条窄窄的石坂桥,走上一条黑黝黝的泥土路,两边是大大小小的蔬菜地,通常种着包菜、莴笋、大蒜、蚕豆之类,都是些大路菜,全眼熟。这里的农民思想有点固执,几乎一成不变地遵守着祖例,爷爷种什么、父亲种什么,他就种什么。冬种麦、夏种稻、年前播蚕豆、过了谷雨插蕃暑,年年如此,不会想着去弄点西芹种种,弄点桂花树种种,弄点玫瑰花种种。一方面是出类拔萃的东西容易遭贼,另一方面也是人心太平,贪安逸,守现成,不愿去动脑筋想门路。
沿着小路往前走,路高高低低不平,山的意思渐渐明显。虽然不高,但已经是山了。途中碰到一条小涧,时而平缓地流着,时而从岩缝时哗哗地冲下来。那水是白色的、冰冷的、新鲜而充满活力的,带着草根和落叶的气息。大约走三里多路,山势时而分开时而合拢,渐渐汇集成一个峡口,宽不过三四十米,一路跟随的小涧在不远处急剧地高声喧哗。斑鸠叫起来了,翠绿色的小鸟在草丛中扑腾,又刷的一声飞走。山更加沉默,马尾松的阴影投在地上只有一小块。一切都惊疑不定地等待着什么。你预感到什么要发生,什么要出现。但你不知道,即使处在一双老虎的阴郁的眼光注视下你也不知道,路旁就伏着一只野猪你也没察觉,整个世界看上去都无动于衷,好像都睡去了,只有太阳是活的,光线会走动,你感觉到有了一个伙伴,但它是漠不关心的。实际上当你在山间走动的时候,有多少双眼睛在注视你,多少双耳朵在倾听:小鸟在树枝上偏着头打量;天空中飞旋的鹰在惴度你的个体;野兔在洞中惊魂未定,脑脯一起一伏;蛇和沙鳅感觉到你的脚步的震动,它们脆弱的小心脏沉受不住,纷纷在草丛中游走。当我们一个人在深山旷野里行走的时候,常常感觉身上发冷,害怕,实际上什么也没有,你感觉到的是寂静带给你的威慑和压力。山不长手不长脚,不会跳出来打你一拳,也不会突然变形成为一个魔鬼,但它那么沉默地坐着,一声不吭,你唱歌它也不笑,你咒骂它也不回声,拳打脚踢也没用,它巨大的阴影一会儿就覆盖了你,你感觉到头发被染绿了,眼睛一片乌黑,除了山什么也看不见,你被山吞噬了,被寂静吞噬了。
出了峡口,按理应该是“眼前一片豁然开朗”,像桃花源一样。但不是。虽然宽了许多,山势稍稍地退开了些,但仍是一条小路,沿山脚一条小溪,路边是一小块一小块种着油菜或小麦的田。但是人顿时轻松了许多,沉重的压迫感消失了,蜜蜂嗡嗡地叫着,油菜花这么香,远处一片茶园随着坡地起伏,一直延伸到山腰。正对着峡口的山峰苑如一只巨大的兔子,仰着头,耳朵微张着,似乎你的脚步声打断了它的午餐。
走了一百来米,过一条小木桥,路忽然左拐,眼前真正地“一片豁然开朗”。一个异常美丽的宽阔的山谷、一座黄墙泥瓦的农家小院、一大片开着繁花的桃林、炊烟和黄狗的叫声呈现在你眼前。我的肥胖的、慈祥的、穿着灰布衣服的外婆听到狗叫声,从灶房里走出来,手搭凉蓬在门前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