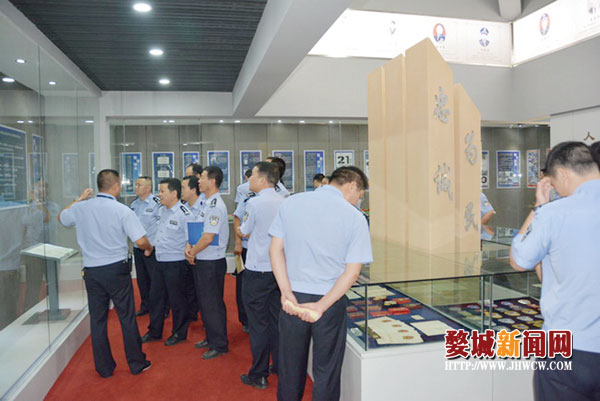一入夏,我就四处找那把伴随我好几个夏天的麦秆扇。妻子笑我,真是不思悔改的老土,家里电风扇、空调都在候着你,偏偏喜欢那山里头的旧东西,这一辈子也摘不掉山里佬的帽子了。说归说,那把芳颜渐褪的麦秆扇总被妻子保管得很好,年年伴我,摇过去一个接一个的酷夏。
每个人的生活体验中,总有一些陪伴自己经历一段岁月的物件,成为那段日子里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些物件不会被岁月的河流冲刷掉,反倒会成为一件整日在手心里摩挲的稀罕物,正如早年间有身份地位人的手玩,愈久弥亮,久藏如新。事实上它们已经渗入到你的灵魂深处,成为你身上暗地里存在的一部分。虽不见出现在视野里,分明像铃铛一样,挂在身上某个地方,以它自己的方式,来提醒你告诉它的存在。于我,譬如麦秆扇。
小时候生活在贫鄙的的山村里,根本看不到电风扇,连电也没供上,更不知道空调为何物。炎夏酷暑,村里人手拿一把麦秆扇,几个人坐在溶溶月色的夏夜里,彼此打着扇,每个人扇出来的风除了扇在自己身上,旁边的人也能享受到一份清凉,围坐在一起,就是一个清凉磁场。我们小孩就在大人的中间钻来钻去,身上爬上爬下,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不闹腾,除了享受大人扇下的清凉,还能听大人们三国西游瞎聊、桑长麻短比较。孩子中间谁的声音吵着大人了,头上、身上就会被大人的扇子拍打,扇子打在身上不痛,大人也不是要打痛你,只是在警告你噤声。遇上顽皮的轻拍几次不听,大人火了,把小孩拉过一旁,调转扇子,用薄竹片削制的扇柄,“啪、啪”打在小屁股上,嘴里就变成轻骂:“叫你吵,大人说话,叫你吵……”,竹片打屁股是很痛的,一般小孩没打两下,就告饶“不吵了,不吵了”,大人也就顺坡而下,收起扇子,又重回聊天乘凉的队伍里。
也有例外的,晒场上一出现了潮水伯的身影,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从各自大人的身边跑开,潮水伯像个大磁块一样,把我们都吸引过去了。潮水伯和我爷爷年纪相仿,我是按字辈称呼他潮水伯。他在村里是个传奇人物,没有读过书,却满嘴西游、三国、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说得唾沫四溅,吸引我们这些小孩子听得如痴如醉。冬春秋我们跑到他家门口去听,夏天的晒谷场,就是潮水伯的说书场。晚饭一过,潮水伯一手提拎着那把油黄发亮的竹椅子,一手摇着他寸步不离的大麦秆扇。说他寸步不离一点不夸张。白天干活时也带在身边,干活时他把大麦秆扇插在后腰上,中途队长安排大家歇乏时,潮水伯就拿出扇子,一个人制造小片清凉。那时大集体,生产队人割完稻谷,男劳力每人一担稻谷挑回晒场。二十几人肩挑一担谷子,在山岭上蜿蜒向上,一字长龙一样,走一段路带头的高叫一声“歇力”,各人就把肩上的担子架到助力的搭柱上,大汗淋漓的大伙儿一个个嘴里直叫热。这时,队伍中就会有特别的一幕出现,潮水伯一个人一手把在搭柱上扶住稻谷担,一手从后腰上拽出麦秆扇,“呼哧呼哧”扇动起来,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夏夜的晒谷场上,潮水伯的麦秆扇不仅仅为了扇风纳凉,更多时候是道具。他呷一口邻家小孩为他端来的茶水,轻咳一声,柔声问我们,昨天讲到哪里了。我们一个个七嘴八舌地抢着说自己记得的段落情节。讲完了,潮水伯对说对的小孩,用扇子轻拍一下,夸一声聪明,对说错的也会用扇子敲一下,嗔一声是不是昨夜听时睡过去梦见娶媳妇了,说完和我们这些屁小孩们一起大声笑起来。笑毕,开讲,手中的大麦秆扇大发神威,潮水伯让扇子跟着自己的讲述指东点西,一会是武器在格斗,一会又是像故事中人物手里的什么器具,害得我们的视线跟着他手中的扇子来回跑,把个小脖子扭得又酸又硬。夜深了,有些大人远远地叫唤自家的孩子回家睡觉。听得入神的我们大多听不见,潮水伯手中的扇子会突然“啪”地打在被叫的小孩的头上,打完后用扇子一指,莫名其妙的小孩顺着潮水伯的扇子方向一看,夜色中正传来家里人的叫唤,就急急地站起跑回家去。晒谷场上的小孩像一茬茬的庄稼,大的成熟成人了,小的青涩稚童又加入队列中,直到潮水伯八十多岁无疾而终。夏夜的晒场上、巷子里、弄堂内,整个村子内外,永远看不见潮水伯那把大麦秆扇的身影了。
我小时候断奶在祖父母身边,祖母对我视同亲生。我的许多同龄人都在嚷嚷夏夜闷热难睡,我却睡得非常安逸。每个晚上我从外面听完潮水伯的故事回家睡觉,一躺下,身旁的祖母就会手执麦秆扇为我扇风,让我安然入睡。偶尔有时半夜热醒,稍一翻动身子,祖母又很快轻摇扇子,直到我重又入睡。可以说,我童年的每一个炎热的夏夜,都是在祖母的挥摇麦秆扇中安逸地度过的。祖母仙逝十余年,我每每在异地他乡辗转难眠时,甚至荒唐地想到,会不会缺少祖母的麦秆扇,害得我人到中年就神经衰弱,没有一宿能够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明自然醒的。为此,我在几年前回家时,特意带了一把扇在身边,让它在他乡异地的夏夜,为我送来家乡的凉风,送来记忆之中那一片无法忘怀的清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