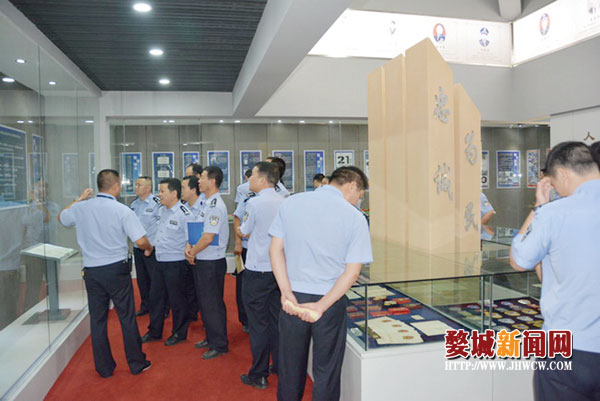一个五十岁的男人还没有结婚,能不能称为老单身汉?对于这个观点他有些飘忽不定,仿佛他一直都生活在年轻的时候;只有当别人不怨其烦地议论他的身事,刚好又被他撞上,那时他才会悲哀地感觉似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再也没有年轻的时候了,一个去年刚成为寡妇的女人好几次这样说他。以至于他一看到她们挨着门墙低声地说话,就会不由自主地虚构那些重复的内容,此时他必须从她们身旁经过,她们停下来以女人的目光看着他;从前,他会点点头示意,也不知从哪次起,他变得像个梦游人一样忽略这些妇女,悄然地踏上通往楼上的阶梯。然而他的心是不平静的,有一次楼下的女人半认真地要把寡妇介绍给他,他委婉地拒绝了,过了许多天,两个女人似乎都忘记这件事情,现在他向她们显现这种表情,是不是会把事情弄得毫无挽回的余地呢?其实那是个非常普通的女人,但事情过了这么多天,那种邂逅式的征求他意见的眼神再也没有出现过,又让他感觉这个寡妇其实也不错。他需要女人,他不想单身终老,好几次他匆匆从楼上下来,刚好迎面遇上她,心居然会砰砰直跳。他暗暗观察过她的胸部和裸露的肌肤,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给人的错觉对他这种没有经验的男人来说是致命的,有时他在她后面上楼,她最美的形象通过扭动的臀部以及结实的大腿传达出让他兴奋的欲念,他真恨不得立即扑上去占有她。但是她回过头来,看到他伪装的淡然神情,也陌生地别过脸去,他又感觉到卑微,幸福已经一去不返了。
当他走进房间,狭小但散满杂物的卧室里,看上去居然好像只有一张床铺和一个衣橱,站在衣橱的镜前留影,或者靠着窗台随意地观望外面,他都能够预感眼下这个居所将会变得更加孤单,真老了的时候,只剩下这个房间了,而这座房子比他年纪小很多,如果它有一天也老了,肯定是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那时他在哪儿呢?天知道。可是活着是需要一个伴的。年轻时他想养几条狗,不过那多半出于物资上的复仇,因为没有女人希望嫁给他,但养狗对他的钱包来说是绰绰有余的,他甚至可以省吃俭用,给它们买优质的口粮。现在这个念头愈发地强烈,哪怕只养一只,随便什么宠物都行,一旦它们愚昧但又温驯地撒动四肢向他乞食,那么作为公寓中的一员、单位里的小职工,他残留的支配心理多少能获得平衡。为此他每天逛宠物市场,穿着他最好的衣服首先出入在本区最高档的两家宠物店;他极力表现出优雅的举止,像个有钱的行家在为自己的小情人选购那样,对宠物只要求美观与健康,钱从来都不是问题;他收集了各方各面的资料,然后攒着这些知识围着笼子细细地比较,漂亮的女售货员们头一次几乎都会被他迷惑得屡屡温柔地向他献殷勤,让他好不得意,他喜欢闻她们身上的香水味,冷不丁地但又温和地和她们谈话,等到她们惊醒了,她们灵敏的嗅觉用不了多长的时间辨出了他,于是鄙夷地一瞥,不再对他感兴趣,最后属于他的便是靠近郊区的、凝滞着动物腐尸及粪便臭气的家禽街。
他倒是喜欢那个片区,只要他一出现,人们都能够认出他,他不再是纯粹的顾客,而是曾经的年轻邮递员,他们的老朋友,因为从十七岁起,他就在这里投递了二十年的信件,到后来通往的信件少了,又招来了投递报纸的临时工,他便坐进办公室享起清福了。人们这样评价他——不幸,还好得到补偿,归根结底又留下了遗憾——他应该结婚的。现在他走在这条街上,像回忆从前的生活,围绕在关着猫和狗的笼子边,他像对待恋人一样随意挑选,只要他看上哪只,店主一定会免费送给他。可是他是没有办法接受那么拥挤的空间里再塞进一个笼子,这算是原因,但最主要的是他觉得这些土猫和土狗都没有一丝高贵的灵性。他从这里走过,从年轻时开始,不知在笼子外观看过多少次了,人们从他认真的神情里看到他的真诚,没有人了解为什么他总是空手而回,还带着失望,他像他的家一样,充满迷雾,而这样又正好使得人更加同情和尊敬他。产生这种情绪是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感觉他缺乏什么呢?人们送给他自产的瓜果和蔬菜,虽然不值钱,但是他们的土地原本就变得非常稀少,他也接受他们的馈赠,总是在某一天的暮色中幽暗地提着,像是个受到诱惑侵害的病人,以至于他无法安置那些最终将脱水的食物——然而,记忆又不堪清晰地告诫他,毫无理由地将这里扩大一万倍,那里抛弃得无影无踪,倘若真相在它需要澄清的第一时间面对他,或者正值一个完全脆弱的人濒临最理智的那一瞬间,他收录得到那些证据,他害怕它们,了解它们,那些营养学的分析、化学式的猜测、甚至是盲目吞咽地在餐桌上处理掉的所有残余,从中得到的满足就是催促他在告别他们时心存怀恨、妒忌和感激。他黯然地走过巷道,他在房间回想他黯然地走过巷道,好像坐享劫后惊魂的余生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