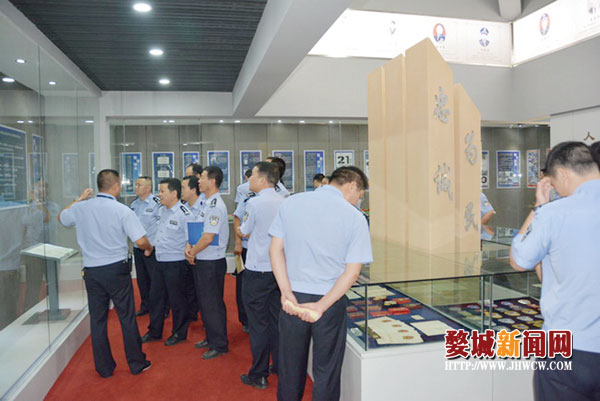“唇舌的授权”很容易让人想到爱尔兰的诺奖诗人西蒙斯·希尼的那篇关于诗歌的著名随笔:舌头的管辖。虽说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大为不同———前者集中在教育领域,后者则发力于诗歌身上———但这两个古怪的“标题”所运用的相同的修辞还是给人的联想提供了捷径。这种联想或许并非毫无道理。回顾一下张文质的大学中文系背景和他的写诗经历,人们或许会为自己的这种联想而略感放心。
“唇舌的授权”这一短语的发明权要归功于作为诗人的张文质,而汇聚到这本书里的其他文字才属于作为教育者的张文质。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短语具有出奇制胜的效果,然后我才要辨别其中艰涩的含义:什么叫唇舌的授权?先来看看书中作者的一段原话:
“我们现在的(教育)写作,往往是一种应付式的,我把它称为命令式的。这种写作,不是出于你内心的触动,不是在你写完以后感觉到是为将帮助我、陪伴我或者认出我是谁的这样一些读者而写。……“授权”,就是要表述一切,要表述在教育领域,在思想领域,在个人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我想,这种表述一切的权利,与那种不断窄化的、特别理性化、技术化、知识化的写作是大相径庭的。越是有批判性的东西,越是有新思想存在的写作,它才有可能触动读者,触动读者的一种回应,一种互动,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交流的欲望。”
这段话大概能让教师们想到每学期必交的论文、案例等,这些出于惯性和形式的行为虽为教师所憎恶和接受,但很少有人作出深刻反省的。长期以来的教育积习使得“教育写作”这样一个命题向着“技术化”和“形式化”的方向不断靠拢,它缺乏新鲜活泼的生命,这正是张文质所厌恶和反对的。因此,他认为教育写作可能是走进了一个误区:
“你不会感到有一种思想在搏击,有一种思想在萌芽,或者有一种思想在诞生,在碰撞,在裂变,这些痕迹都看不到了。”
基于此,张文质认为教育者有必要重新打量“教育写作”,有必要将“教育写作”从公共的写作和话语系统里面剥离出来,来一次“教育写作的自我授权”,即,不需要有规范的模式,做到“我手写我心”即可。这种“授权”来自于“唇舌”,而“唇舌”是自由的,因此我们不妨把“唇舌的授权”理解为:自由表达,真实尖锐。为此,张文质甚至说:
“对于教育写作,我宁愿看到的可能是混乱的、不清晰的,不是那么理性的,但却是真实的尖锐的素质。”
这并非是张文质的矫枉过正,也不是张文质对理性的厌恶,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对“教育写作”中自由、活泼、真实、尖锐、深刻、预见性等优秀品质的极度渴望。
当张文质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和教育界的写作现实后,当他找到了自己的“真理明灯”后,就意味着在思想和理论上他拥有了坚定的方向和基础。解放了头脑之后,就必须解放手脚。换句话来说,在确定了“教育写作”的内容(写什么)后,他还必须要为“教育写作”找一个恰当的形式(怎么写):什么样的形式才符合他所谓写作中的自由、尖锐、深刻?他在《1997年教育手书》里写道:
“1997年6月27日晚,我突然萌生了写一部散乱、随意、信马由缰式教育笔记的念头。它完全来自俄国作家瓦·洛扎诺夫的启迪。……(他的)《落叶集》及《隐居》的片断则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我愿意是这位风格独特、思想深邃的作家拙劣的模仿者。”
在完成了他所想写之书后,他又说:
“洛扎诺夫的《落叶集》则像闪电般照亮了我教育写作的旅途,我的《唇舌的授权》就像是它遥远而笨拙的回声。”
我手里有一本洛扎诺夫的《落叶集》,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它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一部奇书,以“自由、随意”著称,其中多是记载作者的沉思所得,类似蒙田的《随笔集》,但相较于蒙田的《随笔集》,《落叶集》更加短小,甚至凌乱而毫无章法,且没有标题,也许这就是“自由思考”的外在表现吧。张文质通过模仿《落叶集》的外在形式来强化着自己对那种刻板、规范的教育写作的反叛,也强化着自己对自由思考的欣喜。
《唇舌的授权》的内容多为作者日常教育生活中的感思所得,涉及面广而深,“儿童教育是作者笔触最敏感的痛点。”他给我们提供了看教育的三个视角:纯粹学理的;实践的;跳出圈外的。因为对于教育现实了解得过深,所以对于教育充满了深情的忧虑,张文质曾说:“除了是一个忧思者,我可能什么都不是”,但这种忧虑却并没有表现为抱怨,改用诗人艾青的一句话来说是:为什么我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教育爱得深沉。
也正如学者黄克剑所说,对于这本书,“倘若是一位诗人,你也许可以从这里读出别一种诗意;倘是一位不苟的从教者,你也许可以从这里感受得到那种为教育的深情眷注所引发的难以自已的悲剧感。”是的,悲剧感,深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