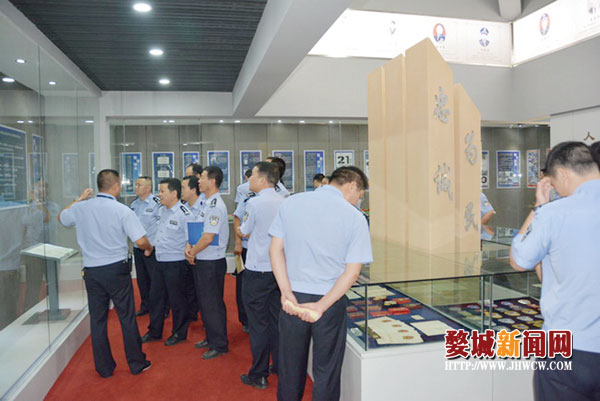近一年来,我再也没有去过野外。过敏症困扰着我,手上、腿上长满了水泡与疙瘩,痒得厉害,最后连法国梧桐的叶子飒飒吹动,我都要心里发憷。我在想,完蛋了。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
夏末,身上稍许好些。我偶尔也出门转转。镇子里的巷子还有些意味。我往往绕远,绕过靖海楼去画廊。檐影交割,晦明相接,风时急时缓,在那里游荡。高颀的水杉隔着院墙,不时把枯干的杉枝掉落在青石板上。这是巷子里的晴日景象。换了阴雨天,两堵高墙湿漉漉地发黑,滑溜溜的巷道像面打磨出来的镜子,光影可鉴。走到巷子尽头,路沉落下去,接到了河边,继而被苇丛捉住,押送到一座小桥,再到桥对岸,一株高大的紫桐前来迎接。路已经变宽了,三岔路口,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直着向前,依次童装铺、香水店、琴行,然后,画廊就在眼前了。
推开风铃垂挂的玻璃门,画廊主人见来了人,即去泡茶。我总是站在逼仄的过道前,先看一下两只鸟儿。去得次数多了,八哥早就不像以前那般兴奋,它在笼子里偏过头来看我,脖子略伸一伸,缩回去了事。喜鹊则是俯低身子,好像随时要冲过来,猛地给我一口。
我并不喜欢这只八哥,画廊主人也不喜欢。它会在喉咙里“哦嗬嗬”、“哇呼呼”地大笑,也会问好,饿了会说“吃~面”,渴了会说“喔(喝)~水”,当然也会说“再见”、“拜拜”。不喜欢的人它是不说的。见它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于是拿根麻秆来逗它,隔着笼栅,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它也把头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摆个不停。它气得浑身发颤,翅羽也全部涨开,终于等到麻秆靠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啄上一口。我心想,有愤怒就好,总比我现在活得连愤怒都几乎快没了的好。游戏到此结束。
换了书店里的老太太过来,那是另外一副德性。老远听到那脚步声过来,它就开始“嗯呜嗯呜”地哼唱,等到老太太推开门进来,马上问好,拿了头和身子在她手上挨挨擦擦,十分地亲热。鸟与人有缘,但要看和谁结缘。她既不养她,也不喂她,它却偏偏和她要好,好得不得了,让人见了眼红。她就问它,“哦,他们欺负你呀。”它就“嗯~哇,嗯~哇”地诉说个不停。至于画廊主人,除了渴了、饿了,它发出命令来指使,把画廊主人当仆从使唤一样,它再也没有多余的话。
隔壁的琴行里有另外一只八哥。当年还是雏儿,台风来临时从苦楝树上掉下来。画廊主人因为早有了一只,也就把它送与琴行主人。它与琴行主人无缘,每天坐等的就是画廊主人过去。忽然有一日,它飞出了笼子,栖在一棵高大的香樟树顶上,再也不肯飞回。于是,琴行主人赶紧打来电话,把下了乡的画廊主人急急叫来。画廊主人把手摊开,“嘘———”地一声口哨,那鸟儿也就欢欣鼓舞地飞来,停落手上,竖起身,轮起翅膀,对着它“叽哇”个不停。说时迟,那时急,手一拢,画廊主人早把它握住,塞入笼中了事。自此,这鸟儿再也不理会画廊主人,任它千百般殷勤,终是偏过头不去觑他一眼。缘分已尽。
画廊主人的这只八哥,现在整天内心郁结,心事重重。除了痴痴地等那个她,它别无它想。主人有时心里薅恼,忍不住会去碰一碰它,它也不吭不啄。终是你养着我吧,也许它是如此想的,任你来吧。但等到他的手一离开笼子,它马上洗澡,用了喙引了水流,把全身上下洗个遍。主人有气,再伸进手去抚摸,它也就再洗。两方像赌了气,如此反复,鸟儿洗过三四回澡,主人终是心里恻然,悻悻然离开。
喜鹊是画廊主人的至爱。自从它掉下巢,主人把它从柴堆里捡起,一点点喂大,它就对主人忠心不贰。没有人敢接近它,它那张嘴啄到手上,完全可以洞穿手掌。野外的喜鹊,它们不乏锻炼,身子精瘦,几乎没有一丝赘肉,我从鸟网与兽夹上解下它们,从头至尾,摸上去就是一把“驳壳枪”。这鸟儿在笼子里长大,虽然个性十分活泼,总是不停地跳跃,啄木头,但身子还是要圆胖一些。它也爱干净,总是及时打理自己的羽毛,十分光洁。但比起野外的鸟儿,终是要差一些。鸟羽上的那种钢灰色,是因为长期飞行,血液通过毛细血管一直尽力送到羽端,焕发出来的颜色。这些螟蛉子的羽毛终是要逊色许多。虽然它的喙一天到晚总是不停地啄磨,如此地尖锐有力,但隔不了多长时日,主人也不得不用剪刀帮它修剪一番。
这鸟儿自知命运,倒把画廊主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主人待它如此之好,它也会帮着主人收拾桌上的小东西,诸如挂件、笔筒、打火机、耳勺,无论主人如何乱丢,它总会叼来,置于一处,暗暗地收藏。笼子门不用铁丝拧上,它也会自己拱开笼门出来,自己进去,玩够了关上笼门。倘若主人要吃牛肉干,它也会帮他剥开,看着他吃下,偶尔也讨主人欢心,尝试着吃上一口两口,待到主人吃完,它就把一张糖纸宝贝似地收藏。它也明知主人不喜欢那只八哥,两只鸟儿若是一齐放出,瞬间它就能骑在八哥身上,作势要啄,只待画廊主人一声令下。主人又哪有那样的心思呢,是它揣摸罢了。看到主人着急的样子,它也就放开八哥,飞到高处炫耀自己的力量。喜鹊的智商竟是如此之高。
海宁有一农户,梨地里的大桑树上有一个鹊巢,人与鸟一直相安无事。一日,农户同帮工在树底下用中餐,聒噪不停。鹊巢中的鸟儿竟然飞出来,在他们头顶上拉下一泡屎。农户窝心不过,用竹竿直接捅翻鸟窝了事。喜鹊是迁居别地了,但事情远远未完。待到梨儿半熟,这只鸟竟然引来一大群喜鹊,在每只梨儿上啄破,不多不少,只啄一洞……我曾在野外看到喜鹊选取配偶的聚会,也曾见到喜鹊送葬的场面,此前有文详述,于兹从略。我是说,喜鹊的智商,相较于人,也毫不亚于。
南门某集贸市场,肉铺主人也养有一只喜鹊。我每见这鸟儿在菜市里厮混,同各个摊主都混得格外熟络,它也会觑乖讨巧,讨要吃食。也许它还知道这菜场里的勾当,竟然会趁别的铺主不注意,偷偷叼了硬币回家。喜鹊对闪闪发光的东西感兴趣,多有在妆台上丢了戒指、铃铛、手串与项链的,恐怕与之也不无干系。如前所述,喜鹊多有人的习性与心智而已。
无论如何,螟蛉子心里恐怕都有自己的隐衷。把它们放出去,也不会和野外的同类混作一群。喜鹊是这样,八哥亦然。它们和自己的同类隔着距离对望,既不呼唤,也不做出某种肢体语言,只是相互凝视一阵,然后各自飞走。这是十分有趣的现象,留待我以后深究。我心下里以为,鸟儿之间应该会感应到对方的体型与力量,对方的生活经历。有没有沾染人的气味,或者说尘世的气味,那可能是最直接也最易感受到的。这些螟蛉子,幼年失怙,如此的生活,怕也是迫不得已了。
云南人某,我见他在花鸟市场一声唿哨,笼子里的画眉便躁动不停,马上朝向他婉转鸣叫,恨不得立刻冲开笼栅,跟着他走。他也十分了得,一般的画眉根本不入法眼,他只是稍作逗弄,便即刻走开。他自述家中有一只画眉,但也不是“顶尖儿”的,虽然那只画眉生活月用都已高过他的用度,他还是有些失落。他去南北湖的山里捉画眉,空手而去,不带任何鸟具,他吹一种奇奇怪怪、低沉又荒落的口哨,就有画眉飞来他的手上。心甘如此地跟随他,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许,他吹的是那雌鸟儿的小曲?好在他只为寻找他心里的那只画眉,从不愿为恶,他端详一下,听一听它的鸣叫,也就叹着气放了手上的鸟儿。